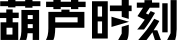晚一天去探望母亲,也不要紧的吧。
父亲很早就过世了,母亲没有再婚,独自照顾乔。她什么事都应付得了,不过总是风风火火的,偶尔还会不打招呼就突然消失一阵子。
幼儿园时,周末就只剩乔和另一个孩子。不久,那孩子的父母来了,抱起她亲了又亲,给她买了比脸还大的彩虹色棒棒糖赔罪。然后,空荡的房间里就只剩下乔,还有不耐烦的阿姨。
小学时,他从夏令营回来,家里没人。钥匙在门口地垫底下,桌上有钱,冰箱里塞满了面包、果汁和牛奶。
中学那次更过分,母亲消失了好几个月。
那么,晚一天去探望母亲,也没关系吧。
母亲一时明白,一时糊涂,只要稍微糊弄一下,等她回到那个混沌的世界,时间便不存在了。她再次醒来时,会看到儿子正守在床边——如果她刚好能认出乔的话。中间的几千千米、数个小时,都不会在她脑子里留下痕迹。
乔心里嘀咕着,决定再试一次——劝母亲接受一个伴者。毕竟,人没办法一辈子都靠自己。
母亲年轻时看起来很独立,似乎永远在工作,永远在追逐自由。也许她不怎么需要乔这个儿子,只把照顾他当作责任—— 一个没有工作重要的责任。
可她毕竟老了。老了,心就会干涸龟裂,从缝隙里长出孤独。何况她不再工作,困在那个小院子里,不能再出去追逐什么自由,当然更加容易孤独。
乔相信,母亲只要试一次,就一定会爱上伴者。他劝过很多次,劝被困住的母亲通过伴者去再次享受曾有过的自由。事实证明,他低估了老人家的固执,低估了母亲对新事物的戒备。
有那么一回,母亲略显轻蔑地说:“我懂,我懂。伴者啊,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”乔刚想追问和反驳,母亲却像突然想起了什么,转移了话题。
眼前散乱一地的行李令人心烦,乔决定离开这个世界。
零下一百多摄氏度,寒风漫卷着对人来说有剧毒的紫色晶尘,乔感受到的却是温暖和芬芳。眼前是一团团如蓝色泥巴般的东西,一股原始的进食冲动袭来。
吃掉它,然后前进,去吃下一格里的蓝色泥巴。每蠕动一次,前进相同的距离,得到等量的食物,就像是骰子只能掷出一点的飞行棋。吃掉一份食物,就得到精准的一份饱足感,永远不会发生“第七个包子吃饱了,前六个包子白吃了”的情况。
周围的生物个体长得几乎一样,只有大小的线性差别。
不用照镜子,乔也知道自己的伴者不会例外。在这里,物种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太过简单,导致物种多样性彻底消失,只剩下线性虫。乔可以通过每只线性虫的大小估算它们的年龄,因为它们匀速生长。如果有一天,线性虫停止生长,那意味着它已经长到最大,而不是正在经历什么平台期。
那里没有人类所谓的创新和艺术,但有着另外一种简约和规律的美感。选择伴者及其所在的星球时,乔看中的就是这点。至于伴者在8光分还是4.2光年之外,一点都不重要。乔需要的,就是伴者的感官传递给他的这种确定性,这种井井有条,这种二二得四。
乔的工作是想出各种光怪陆离的点子,撬动商业上的指数增长。他最为成功的案例,莫过于对伴者的宣传。
“伴者”是人类与外星生物建立的感知连接,是一种实时神经同步。一旦绑定,人便不再是旁观者,而是以外星生物的感官呼吸、凝视、震颤,在它的脉搏里感知潮汐,在它的神经末梢上触碰宇宙的寒热。
要向人类描述一种非人类的体验,本就是很难做到的事。如何向一条深海里的鱼解释体重?又如何对天生失明者描述颜色?
人们试遍了各种手段,想勾勒出伴者的轮廓,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。图像太静,动画太假,气味会消散,全息投影也不过是光的游戏。
直到乔写下了——
去黑洞边缘,泡一场泥浴。
伽马射线暴马杀鸡:宇宙最锋利的吻,落在背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液态甲烷舒芙蕾:零下两百摄氏度也能入口即化的甜。
文字,这个被遗忘在数据洪流角落的古老工具,重新散发出巫术的力量,将伴者嵌入人类欲望的凹槽。不解释,不还原,而是用荒诞的熟悉感,牵引出人心深处对未知的悸动。
有人花了大价钱去尝鲜,然后逢人便说,伴者带来的感受跟广告语里写的一模一样。可实际上,写下广告语的乔,未曾连接那些伴者。
竞争对手迅速响应,纷纷有样学样,乔则带领公司稳稳守住了领先地位。
可尽管他擅长应对工作上的挑战,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疲惫。毕竟,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人类社会里,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正比。
每个月,乔都得花费两天时间去探望母亲。单程飞几千千米,六个小时,跨越四个时区,然后在老年公寓守上一天,再返回。一天中,母亲状况好的话,大概也只会清醒四五个小时。而这四五个小时里,除了陪伴和慰藉之外,偶尔还会带来新的裂痕和伤害。
乔觉得不划算,却别无他法。好在,乔的伴者栖居的那片异星世界,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刻板的可预测性——正因如此,才令人安心。
几年来,乔每次都按时探望母亲。只有这一次例外。
赶上超新星伴者三十周年庆典活动,公司理所当然地接到了大单子。光是预付金额,就让公司上下如同打了鸡血一般高速运转起来。乔作为策划部门的经理,更是忙疯了。他在意的不光是眼下的经济效益,更重要的是与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联系。
这一忙起来,就忙到忘了吃饭,忘了下班,忘了时间……也忘了打个电话知会一声,说要晚一天去探望母亲。
结果,老年公寓的电话主动打来了。
去机场的路上,到处都是超新星伴者三十周年庆典相关的宣传物料。有贴在汽车椅背上的,也有从车窗外掠过的路边灯箱和更远处的巨幅海报。到了机场,就更多了。从候机厅大屏幕的滚动播出,到飞机尾部的涂装,随处可见。
粗略一算,这些宣传设计有至少四成出自乔所在的公司。
这一切让乔紧张,仿佛他正被工作层层包裹。他踱到自动贩卖机前,拉开柜门,看了眼瓶装水。瓶子上印着红彤彤的“三十周年”,价钱是外面的三倍有余。
虽说以乔的收入,完全不用顾及这些小钱,但他厌恶这种溢价。越是深谙商业手段,就越是难以接受被用在了自己身上。
乔正要把水放回去,却被瓶子背面的图案牢牢吸引。
是他无比熟悉的形象——超新星伴者的主体。三十年前,普通人第一次知晓伴者技术,正是通过她与她的伴者。
那时候,捕获和连接伴者的成本还很高,所以一般只用于宇宙探索。
找到一只皮糙肉厚、对外界严酷环境耐受力极高的外星生物,便可以经由它的身体和感知来触碰宇宙里的禁区。它们身体的强度远胜过钛合金。最重要的是,跟伴者的感应连接不仅不受距离限制,甚至不会被任何物质现象干扰。
那位宇航员背负着探索超新星爆发的挑战。她的伴者被称为独角兽,后来又被描绘成一匹长着巨大彩色双翅的飞马。
现在,已经没人知道宇航员本人身在何处,倒是随处都能看到她头戴面罩、身穿战衣的形象。尤其是三十周年盛典上的全新绘制:一身超级英雄的打扮,骑着独角兽,手持战矛,正要去挑战风车上呼呼旋转的巨大火球。
三十年来,乔越发笃定,自己与伴者技术之间,有种神秘而持久的引力。
十六岁那年,伴者还处在政府垄断示范的阶段。大多数人只能远远观望,乔却拥有了自己的伴者配额——是母亲托人从黑市上弄来的。那时他性情孤僻,母子关系也十分紧绷,偏又赶上母亲的偏头痛频繁发作,不得不一次次住进医院。某个深夜,她躺在病床上,虚弱地对儿子说:“挑一个吧,让它替妈妈守着你……”
乔那时选中的可不是线形虫,而是只“普通”的外星生物,一只外星的“虎”,处于那个星球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