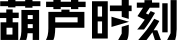月光还是当年的月光
暮春时节的温州,整座城市都浸泡在一种潮湿的、带着樟脑香气的记忆里。我抱着文件疾行在解放街上,梧桐絮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舞者在四月的暖风中打着旋儿,有几片梧桐絮甚至顽皮地钻进我的衣领。就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,一阵裹挟着瓯江潮气的海风突然将我拽住,四营堂巷口,一株百年紫藤正上演着死亡与新生。
那些垂落的花穗像是被谁剪碎了的晚霞,每一朵小花都在用尽全力绽放最后的美丽。我伸手接住一串将坠的花穗,指尖上传来花穗生命的余温。花瓣上细密的纹路,分明是时光用刻刀留下的印记。
巷子深处,常春藤正在攀爬一堵老墙。新生的嫩叶像婴儿攥紧的拳头,老叶则像老人松弛的皮肤,层层叠叠地覆盖着砖石的伤痕。阳光穿过叶隙,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我的脚步声惊飞一群麻雀,它们扑棱棱飞走时落下几片灰褐色的羽毛。
朱自清旧居的门匾安静地悬在门楣上,乌木的底色沉淀着近百年的光阴。我凝视着门环上孔雀蓝的铜绿,突然意识到这抹色彩与《荷塘月色》里描写的“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有着某种神秘的呼应。门槛中央的凹痕里积着昨夜的雨水,倒映出一小片变形的天空。
我推开院门的瞬间,一阵穿堂风挟着梅花的冷香扑面而来。天井里的老梅树扭曲着枝干,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挣扎。树下的石桌上,那个圆形的茶渍像一轮被囚禁的月亮。

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
去登录
本文刊登于《知识窗》2026年1期
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
更多文章来自

订阅